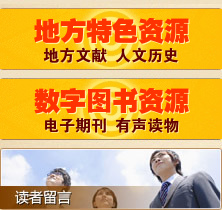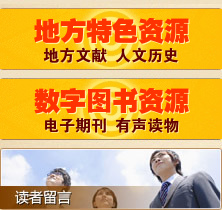1948年,“金翼”之家缔造者林孝先(即《金翼》中的主人公黄东林)全家合影。前排左7为林孝先,左6为其妻郑月娇,左8为林孝先的儿子“三哥”林升华,左9为“四哥”林兴华,后排左7为刚刚大婚的林荣昌,是“四哥”林兴华的儿子。 本报记者 方光明 翻拍

2009年8月6日,福建古田,林孝先部分后代留影。中排左3为84岁的林荣昌,左2为林荣昌之子林应芳,左1为林应芳之妻,后排左2为林应芳儿媳,左3为林应芳儿子。前排为林荣昌曾孙和曾孙女。 本报记者 方光明 摄

《金翼》作者林耀华全家合影(摄于1947年燕京大学)。 本报记者 方光明 翻拍

2009年8月6日,84岁的林荣昌老人和儿子林应芳合影,身后的祖屋就是他们引以为 豪 的“ 金翼”之家。 本报记者 方光明 摄

福建岭尾村
《金翼》简介 上世纪4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教授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讲述上世纪初至30年代福建闽江下游“黄村”发生的故事。《金翼》写的是林耀华家族的事情,文中“金翼”之家的缔造者黄东林即他的父亲林孝先,“小哥”就是林耀华自己,“黄村”如今是福建古田县黄田镇凤亭村之下的自然村——— 岭尾村。40多年后,林耀华的学生庄孔韶又写了《金翼》的续篇《银翅》,是对“黄村”的二次考察。
“金翼”之家的祖屋破败了,围墙上斑驳的白灰提醒每一位来访者,它曾经历的兴衰荣辱。70多年前,从这座大屋里走出的后人林耀华写就的一本人类学著作《金翼》,让这个家族在半个世纪中牵引着中外学者探访的目光。
《金翼》写的是人类学家林耀华家族的事,林耀华即《金翼》中的“小哥”。这本书讲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福建省闽江流域的一介农人,如何利用闽江流域商贸、船运的机遇,将亦农亦商的事业发展至顶峰,继而编织起的一个兴旺家族网络。该书以小说体的形式呈现,但却不失真实性,所用材料基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他在1936年、1937年两次返乡所作的田野调查。
在书中被称为“黄村”的这个村庄,如今真实名字叫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黄田镇凤亭村之下的自然村———岭尾村。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贫苦农民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在疾风骤雨的运动中,金翼之家遭遇巨大变革,昔日以宗族为核心的村庄,阶级阵线取代了宗族组织,主导着村庄乃至金翼之家的农人生活。
70年代以后,出乎意料的是,金翼之家和它的村庄,却家家户户发展起了一项新生计———“银耳经济”,在再次蹿出农业系统过程中获得了成功。这个为人类学家所青睐的田野调查样本,在60年的风风雨雨中,成为中国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变迁的一个缩影。
今日“黄村”
2009年7月,福建宁德市古田县凤亭村。寂静山谷中,一条两车道的水泥路将村落一分为二,南北行驶的卡车,驮着大包小包的棉籽壳和银耳,一来一去,扬起阵阵尘埃,路边郁郁葱葱的竹林和茂盛的草丛蒙上一层厚厚灰尘。
如果不是那长着枪眼高耸的塔楼,我们一定会错过了此行的目的地。金翼民居就位于山谷西南角的台地上,这座依山而建瓦顶夯土式围墙建筑,屋子前后耸立两座用于抵御土匪的塔楼,从水泥路峰回路转,当年恰临土匪出没的荒凉莪洋不远。
87岁的林仁盐,昔日金翼之家的长工,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当年如何在两座塔楼把土匪赶走,塔楼上有大大小小用途不一的枪眼,其中一个洞口最为有趣,因为它有一条管子直通到正大门,土匪来敲门,直接浇上开水就能把他们烫得哇哇叫。
不难想象,当年新居落成时有多威严,即使在今日,它仍是村里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建筑。但数十年过去,围墙上的白灰层已有不少剥落,正门通道长满了比人还高的杂草,如今来访者只能从侧门通行。
84岁的林荣昌老人,摇着蒲扇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他的祖父林孝先(即《金翼》中的主人公黄东林)是金翼之家的缔造者,但在60多年的时间长河中,这里并不是他们的栖身之地。
上世纪30年代,生活在山峦谷底中的古田人筹资修起了一条“西路”,打通了谷口镇和古田县城的交通。林孝先与姐夫张芬洲(《金翼》中的化名,因为他很早就死了,村里的人不知道其真实名字)敏锐地发现,西路打通后与闽江船运联成一线,必将带来谷口镇的繁华,他与姐夫走进了离岭尾村26公里的谷口镇和更远的福州城,联手做起了贩卖咸鱼和稻米的买卖,短短几年间,原本只是面朝土地背朝天的农人,积攒起人生的第一桶金。
金翼之家建立之日,距离新政权到来尚有10余年。其间,林孝先经历了官司诉讼、土匪来袭、店铺分家、地方军政势力刁难等困扰,但最终却总能化险为夷,整个家族变得更团结强大。
1936年、1937年,已经获得北平燕京大学硕士学位的林耀华返回家中,做了两次田野调查。1940年,林耀华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但因妻子治病而滞留,闲暇时间,他以文学体裁撰写了这个家族的兴衰故事,林孝先成了《金翼》中的主人公黄东林。
这部带有“信笔而就”味道的16万字小册子,在西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作者的预期,当时著名人类学家费斯赞誉为:“如竹叶一般,它简朴的形式下却隐藏着高度的艺术。”国外学者视其为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镇社会的首选人类学著作之一。
“金翼”崛起
“金翼”之家称呼的由来,充满了唯心主义的传奇色彩。
做生意使两个姻亲兄弟积攒了不少钱,像大多数传统闽人家庭,林孝先和姐夫张芬洲首先想到盖起自己的新居。两人共同勘测和选择理想房址,姐夫张芬洲被风水先生称为“龙吐珠”的一块风水宝地迷住了,他瞒着林孝先抢先占据了这块“风水”宝地,这使得林孝先大为不满。
出于亲族关系之无奈,林孝先虽然不满,却也只好另择基地,最终他在姐夫房址的另一侧物色了一块坡地盖房。
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张芬洲家刚好在龙头山前谷底少有的平地上,与“龙吐珠”的风水景观说十分吻合,大大优于后来建在山坡上的林孝先家的房址,这预示着芬洲家有着美好的前程。
然而,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这以后两边的家庭都遇到了很多困难,芬洲先遭遇丧子、丧妻等家庭事务的困境,继而又因无从适应店铺的经营关系变化,不得不退出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谷口店铺生意,芬洲的儿子最后又因失误和无能丢掉了再立新业的机会。
与此相反的是,林孝先却总能转危为安,最后当林孝先在福州大摆寿宴时,张芬洲唯一剩下的儿子茂衡却孤独地死去了。
龙吐珠的风水为何不能给芬洲带来好运?这时,风水先生又换了不同的解释,这块“龙吐珠”的宝地已被横穿龙头山的西路给毁了。西路像一把剑,斩断了龙脊,龙因此死掉了,这块地也成了不祥之地。
对林家的兴起,在《金翼》中有过这样的记录,林孝先的儿子林升华,一个接受了教会学校熏陶的年轻人,带着同学香凯来家中做客,讨人喜欢的香凯在爬山时,发现了林家屋后的山状似山鸡,一只金色翅膀伸向黄家房屋,于是他用羽翼荫护来解释兴旺起来的“金翼”之家,这也正是“金翼”之家名字的由来。
“金翼”之家的故事只记录到30年代末日寇来袭就戛然而止,“金翼荫护”的传奇留给了学者探访的冲动,但好运似乎却没有能够眷顾这个家庭下一个十年。
暴风骤雨
在巨大的社会变革进行时,林荣昌还不明白这对他这位“大少爷”意味着什么。1948年,民国37年,23岁的林荣昌大婚,宴开三十多席,在福建南平当大学教授的三叔林升华还请来了专业的摄影师,在金翼祖屋前,族人留下喜气洋洋的合影。
这一次的合影记录的是这个家族最后的辉煌。
1949年6月,从山西省平顺县南下的共产党干部和解放军与古田地下党、地方游击队的指挥者共同组成了新政权。像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等待岭尾村农人的是一场面对面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林荣昌清楚地记得,1950年夏天,小叔林耀华回家了,他是收到三叔林升华“母亲病危”的电报而匆匆赶来。
当他心情沉重返回家中,却发现母亲并未生病,他十分生气而愕然。林升华告诉林耀华,村里土改风声日紧,手中握有上百亩农田和山林的四哥林兴华(林荣昌的父亲)处境很糟糕,三哥希望以林耀华的身份能回乡找熟人说情。
金翼之家培养的两个才子,“小哥”林耀华此时正在学习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毛泽东的讲话《将革命进行到底》,“三哥”林升华留洋归来后曾在一所教会大学任职,新政权成立后被送到福州革命大学短期教育,革命大学的再教育使他明了福建土地改革的步骤已环环相扣,势如破竹。但继承父亲林孝先衣钵的“四哥”从抗战以来渐渐发迹,他利用苛刻的租佃与私人借贷方式沉溺于扩张土地,却丝毫没有预感到脚下已孕育着的烈焰。
第二天,林耀华陪同四哥去谷口镇拜访了区委的领导,但此次返乡之行并没有对改变四哥命运起到什么作用。1951年1月5日,在小哥离开家乡半年之后,一支土地改革工作队进了村。
根据当时当地地主每户所有土地的平均数量衡量,以及解放前3年的时间量比较,四哥的土地已大大超过划为地主的规定,时限又刚好在40年代的最后5年中。几次斗争会之后,阶级成分张榜公布,金翼之家被定为“地主”,而四哥则是地主中的“恶霸地主”被人民法庭押走。
不久,一个消息传到了村庄,四哥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消息传来,金翼之家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他本可以不死的,可工作组说有人命案,实际上是村里有个人死了,我父亲好心给他买了棺木,就被安插了这个罪名。”时过近60年,林荣昌说起父亲之死仍耿耿于怀。
但1986年林耀华的学生庄孔韶回访村里老人时记录下的却是另一番见解。当年60多岁的老人黄学友(化名)说:“被占了田的农人揭发他,连同宗的人也指责他,谷口镇的少扬是个老实人,在店里总受气,所以在解放之初,少扬妻一点也不饶他,揭他的老底,向他索还田地的人都成了控诉地主大会的积极分子。”
中国乡里社会具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原本念在同宗的情分,即使控诉也不会太过分,但让四哥失望的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了。
“当时土改政策定了成分,乡民们唯恐表现不积极,有句话就叫‘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向地主阶级来一个大进军’。”村里老人回忆道。
宗族、家族内外的利益恩怨之争在遇到阶级战线时已混为一谈,它最终没有改变四哥的命运。
金翼折翅
四哥的死成为一桩难以说清的案件,但一个事实是,岭尾村的生活格局已经完全不同于往日。政权是共产党和贫雇农的政权,昔日踌躇满志往返于福州、谷口,不断扩大土地和店铺生意的四哥忽然消失在生活的画面外,好风水象征的“金翼”之家,还有成功者象征的林孝先及其后代,胆怯地隐居着。
林荣昌回忆道,当时全家近20口人被赶到了金翼之家搬迁前的老宅,因为被划为“地主”成分,他们能分到的就是山上最差的一小块土地,还有每人50斤的谷子。
和金翼之家的惶恐不同,翻身做主的农人是带着诚心诚意的喜悦迎接新的政权。
粉碎了旧日的土地制度,确定了地权,连村里的妇女乃至童养媳都获得了土地证,这在传统父系社会的中国是亘古未有的,有了土地的农人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当地的数据统计,岭尾村所在的戍区的水稻作业平均亩产236斤,与战前最高年产量301斤和最低年产量191斤的平均值246斤相比已相差不多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老人们记得,村里的红旗上写着“抗美援朝”的字句,互助组田地里插着红旗和“爱国增产”标语牌,甚至在农具木柄上刻“爱国增产”的字样以示决心。
被赶出金翼祖屋的金翼后人自是受尽冷眼。在新的政治原则下,金翼之家的内外关系首先已不是叔侄、舅甥的关系,而是地主与中农、贫农的关系,地主自食其力自不用说,当时如火如荼的互助组是不能、也不敢接纳地主家族的,“那时村里人谁都不愿搭理咱家,”林荣昌的儿子林应芳对童年的印象一直停留着母亲上山砍木柴来养活家人的画面。
互助组的热情并没有多长,50年代末国家急于发展重工业,从农业积累资金,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跃进的时期。
1954年仅岭尾村所在的山谷一下子就产生出了5个初级生产合作社:群承合作社、群力合作社、群建合作社、前途合作社和希望合作社。一年多后,它们又被合并为前途高级社,与此前不同的是,社员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刚刚才分给个人的东西,没几天就充公了,社员们思想上想不通了,合作社为了给社员分红,不得不上山砍树。
“1956年以前你来这里,山上都是树,两侧山上的树涛声大得吓人。”当年的土改干部黄孝秀(化名)在80年代时接受庄孔韶回访时总结道,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对当地最大的伤害莫过于对山林的砍伐,1958年,村民们忽视了山林的再生限度,山谷两侧的砍伐浪潮达到一个巅峰,大炼钢铁、烧炭、毁树种粮都必须大量砍伐森林,山岭变成了“癞痢头”,这使得在后来多年水土流失严重,河流水库淤积又导致山塘水库连连报废。
1965年,92岁的金翼家长林孝先辞世,在经历大半生辛劳后,他见证这个家族从贫困走向辉煌又再次陷入困顿的生活,晚年的他一直沉默,没有给儿女留下什么遗言。
“银翅”展开
1970年前后,“文化大革命”中的城市还在闹腾,在闽江流域的村庄,农民已经厌倦了暴风骤雨的运动,饿着肚子的农民四处寻找着机会。
林荣昌的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一天天长大了,他面临的苦恼是,仄逼的房子如何容纳这么多口人,他和几个儿子到山上砍伐杉木想盖房子,但因为“地主”成分,盖房被村委会叫停了,最后杉木被上缴了。
在古田的女儿此时却捎来消息,说县城里有人在种一种叫银耳的东西,很好赚钱,虽然对这个新东西一无所知,但此时窘迫的林荣昌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与三个儿子决定试手一干。
关于银耳在古田县的扎根,如今听起来确实是个传奇,从一穷二白的山区县,到成为“中国食用菌之都”(古田县目前生产的银耳占了世界产量的90%,占全中国的95%),古田只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如今在古田,几乎每户家庭都对银耳的故事耳熟能详。1969年,古田县一个叫姚淑先的年轻人偶然在枫树上发现一朵7层的大银耳,周围潮湿的气候,林中的散射光,深山里的新鲜空气,形成了巨耳子实体分化的最佳条件,这让他产生了用人工创造模拟环境培育银耳的想法。但他的试验直到1977年才真正获得成功,那一次姚淑先代料栽培的5000瓶银耳大丰收,获利甚多。求教的农人纷至沓来,是按照传统秘而不宣,还是公之于众,姚淑先选择了把技术向世代务农的乡里人开放。1981年,福建省委书记项南视察了他的工厂,《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均以显著位置报道过他的故事。
代料取代原木,这个里程碑式的创举,造就了古田后来蓬勃发展的食用菌产业,70年代末,岭尾村农人也被卷入了这场食用革命。
虽然比其他家穷,但林荣昌家令人羡慕的是,他有着三个能干的儿子和四个巧干的女儿。
银耳栽培在农忙季节结束后进行,普通农家每年能种三四批,但劳动力多的林荣昌一家可以做到10批以上。“银耳有个好处,三四十天就能完成一批,我们家三兄弟一起做,第一次就赚了一千多块钱,那时在生产队赚工分,三个劳动力一天也就赚1块钱,365天就是365元,当时一下子拿到那么多钱,想想真是赚翻了!”回忆赚取第一桶金的历程,林荣昌的儿子林应芳至今仍喜得合不拢嘴。
听说外地银耳能卖好价钱,80年代初,林应芳和同乡同行第一次做坐上火车,跑起了“推销”,他们的足迹走过了福州、北京、广州、沈阳等中国多个城市。
在几十年后,族人间曾经的隔阂却因一项生计在淡去。“当时大家连福州城都没有去过,心中不免发慌,何况是大城市,”林应芳回忆道,这个30年来的第一次个体推销活动首站就是广州,聚集了三四十个同行,浩浩荡荡出行。“银耳经济”让金翼之家生活正朝着一条向上的曲线前行,林应芳说他第一次感觉到,“地主”的身份不再是扎眼的标签,他的族人已经能够接受他们了。
在80年代中期,荣昌家已经能买起一部14000元的胶轮拖拉机来运输银耳,这也是村庄里买车的最高价,这次他们得到的更是村里啧啧的赞叹声。
岭尾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起了银耳,1986年冬季,庄孔韶回访岭尾村,记下了这番令他激动的景象:“入冬的一天晚上,月明星稀,我从黄村山岗农家做客出来,站在高高的泥土路上,吸一口清凉的空气。眼望橄榄状的山谷,看到黄村农家门前、道边晾着白木耳的竹草席还未收起,上面密布的白木耳层和月光交相映照,狭长的一片又一片,像无数舒展的银色翅膀。”
“昔日的金翼消失了,幸运的银翅又降落在这同一块土地上,”——— 庄孔韶在《银翅》中感性地写道。
宗族远去
沉寂了60多年后,金翼之家和外界又开始了联系,当年曾经作为一条商旅要道的“西路”,再次成为金翼之家农村生活与商业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
60年间,金翼之家所在的岭尾村大致保持原有的风貌,但其周围却发生了称得上“翻天覆地”的变化。1958年和1989年,因国家建设古田溪水电站和水口水电站,古田县库区大移民共计63000人,先后淹没一座千年古城和69个村(居),古田人两次牺牲自己的家园,成为全国少有、福建仅有的重点库区县,而这其中就包括在《金翼》小说中曾经喧嚣繁华的谷口镇。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被西路斩断龙脉的“龙吐珠”张芬洲宅地,上世纪五十年代作为库区移民搬迁点被占用,到1989年水口水库修成后,这里又被认为是地质灾害点被拆除,移民再次被分散到小村的各个角落。
如今的岭尾村已不再是林家姻亲组成的大家族单姓村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既有像林荣昌这样的本土居民,也有重建家园后的库区移民,从五十年代起,新旧居民一直和睦相处,从未发生过宗族械斗,这一点倒与南方农村近年来日益抬头的宗族势力复兴情形大为迥异。
林荣昌告诉记者,林氏唯一的一本族谱在“文革”中曾被烧毁。但他并没有要重修族谱的打算,这几年令他比较满意的是族人把村内的一座敬奉陈婧姑的庙宇重修,每年的正月初九,村民们去镇上请神,这是一年里村庄最大的节日。
林荣昌还念念不忘一件事,他的祖父亲手缔造的金翼祖屋,是否还有机会拿回来?
和长辈们不同,林荣昌的孙辈们对生计等现实的事情更有热情。林应芳的几个儿子走了一条和他不同的路子。前几年,村里有人去江西学习了做瓦罐汤的技术,在福州的一些高校开起了小档口,没想到效益不错,岭尾村不少农人便放弃了银耳生计,纷纷做起了小档口的生意。
“现在做银耳都是要有技术,小打小闹赚不了大钱。”林应芳告诉记者,村里人觉得还不如出去做生意好。
炎热的七月,山谷里吹来清爽的风,村庄路口的杂货铺居然人头涌涌。“你如果平时来肯定找不到几个人,现在放暑假,大家都回来,开学了再回去。”凤亭村的村主任林芳贤告诉记者,整个凤亭村1692人400多户,如今三分之一的人做“银耳”,三分之一的人在做“瓦罐”,还有三分之一种经济作物,像荣昌家就有四户在做瓦罐生意,“出去开店一年赚十万没问题,但散户做银耳就不能保证了。”
村里人最近还在热议的一件事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京福高铁合(肥)福(州)客运专线,已通过国家发改委的预先可行性报告,如果工程可行性报告完成的话,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动工,修建后的高铁站距离古田县城仅17公里,距离岭尾村更只有4公里,可以预想它给古田乃至岭尾的村民带来的是怎样的机遇。虽然至今村里人尚无一人读过《金翼》这本书,但村民仍笃信风水,先祖开辟的这块土地给他们留下的福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