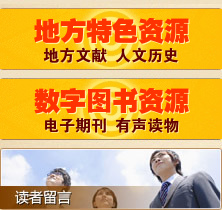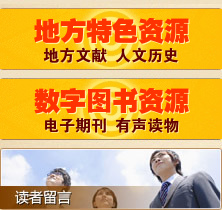|
|
|
|
|
|
1951年,建设古田溪水电站的消息,传遍全县。许多青年农民一下子变成新一代产业工人,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手执铁锤、肩扛钢钎的形象,很让大家羡慕。我童年的几个朋友,也参加了电站建设。待到建设电站的全部蓝图出来后,大家才知道沿古田溪要建设多级电站,还要建大水库,还要迁城移民。
消息成为现实
1958年,是大跃进的头一年。旧县城就要搬迁了,城郊的乡村也在准备搬迁。有一天,县移民处组织城关各机关、学校、团体列队欢送南门村移民搬迁的队伍。腰鼓声、鞭炮声震天响,隆重揭开了移民的序幕。同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标语随处可见,更激励着水电站建设者日夜奋战。白天,红旗飘舞,个个你追我赶,不甘示弱;晚上,灯火通明,人人手忙脚快,争先恐后。剑溪两岸到处是紧张繁忙景象。
接着,四五十个小乡村移民工作全面铺开。我的老家——沂洋是库区东边最大的一个乡村,
全村在“三八二”淹没线以内的占五分之四多,村前七大田洋,即牛栏洋、后坂洋、过溪洋、楼下洋、西安洋、蒋墘洋、溪边洋都在淹没范围。沂洋溪沿岸一马平川,是千百年来两溪交汇所形成的冲积平原,更是稻麦豆、稻麦花生三收之地,是本县糯米、小麦、黄豆、花生的丰产区。此外,沿溪沙坂几百亩“白面桃”也被淹,只留下村后昆山脚下几片无雨就旱、一年一收的山田。因此,人们都把自己的心弦绊在“三八二”线上。有人竟为此向菩萨求助,希望自己的家划在淹没线上。说来好笑,连“孔夫子”、“城隍爷”都要搬迁,大小庙宇的神自己都不知去向何处,哪还顾得上凡人。
移民工作组进村
家是老家好,月是故乡圆。要说服许多人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故土,确实十分困难,必须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物质准备。工作组来到沂洋,叫各姓(七个姓)推举几个代表共商搬迁事宜。动员大会上,工作组同志说明了移民的目的意义后,让大家讨论,提意见和要求。
有人说:“要原拆原建,一姓一族住在一起。”
“天下农民是一家,还分什么一姓一族呢?这是落后思想!”不知谁顶了一句。
有的人要求后靠。工作组宣布:“三八二”以上的住户,如果没有房屋、田地,不能后靠。又说:“附近乡村有亲戚,
可以投亲靠戚。”落实后,我两房同宗的十几户除了两家亲戚有待联系,其他的通通都是移民户。父亲是移民代表,要求随子生活,不要国家负担。会后,叔父们议论:“反正国家拆,国家建,国家安置。别人怎样,我们也怎样。”“有一个能蔽风雨、防寒暑的去处就可以,何必多讲。”几个婶婶却不以为然,要找工作组去理论,要求搬到曲埕楼去。曲埕楼是我家制曲的温室,也是我家在淹没地以上的房屋。不知工作组的老黄如何说服她们。老黄是我的老同学,初出茅庐,却很有磨嘴皮的功夫。
拆旧房建新房
沂洋村淹没地“新厝境”,有11幢只用了50多年的大房子,面积相仿、格局相同,全都是一宅两院,其中以王家大院(一宅三院)最气派。为了建移民新厝,就地取材,决定这一片的房屋先拆。
大跃进的号角一阵紧似一阵,移民搬迁的命令如山倒,说搬就搬。我家房屋是最早搬迁的,很多家俱都暂寄在同宗的堂屋内(后拆),先搬的只是日常的食、宿、生产用具,如箱柜、锅碗、锄头之类。至于堂屋内公共的长几、圈椅、八仙桌、大门灯、石舂、石磨、石井栏,停放在阁楼上的造酒、制曲、织麻、纺麻等系列竹木器具,甚至连犁、耙、风车、水车、大小粪桶等家具、农具,都横七竖八地摔在地上和公路(福古路)旁。“物是小可,置是艰难”千年家训,此时谁也不提了。
我家屋子是第一天开拆,计12丈深、5丈宽,左边前面高墙周陈,共有两层楼上楼下18个房间。同屋的叔伯姆婶们,个个感到难过,可谁也不说,各自避开(当时的现场照片还留在某干部手上)。邻居曾婶婆前一天便赶往福州儿媳家,因为她听说要拆房子心里受不了,眼不见,心不伤。父亲与老房子同龄,他先抽空到新城看了一下,大发感慨:“有福之人住城市。”
沂洋村党支部、社队组织仍保留着,一方面要送走移民户,一方面要安置后靠户,任务不轻。要抓紧建造后靠移民厝,利用先拆的旧木料重新组合一幢新屋,再修补一幢百年六扇厝——荒厝。为了赶时间完成任务,把我家的大门(相思木)、正门(铁柴),原封不动地安在两处移民厝上,至今还在。
转眼已是初冬,我带领一中学生从临水洗铁沙回城时,顺便回家看看,老家已是人去楼拆,空空如也。
计有:五户迁往大桥宅里,两户迁往大桥桃坪亭、吉巷上元靠亲,一个瞎眼睛的老伯母跟女儿迁鹤塘去了,后靠的是两个五保户。
意义双关的移民灶
操办全民食堂的时候,对移民户要不要建灶之事,大家争论不休。青年人说:“吃食堂,省了砍柴工。”当家的说:“开门七件事,事事操心,不建灶,也省工夫。”五保户说:“每日三餐要拄着拐棍吃饭不方便,要汤要茶怎么办?雨天黑夜怎么办?”。年老的说:“移了民、没了灶,不吉利!”老支书听了也动心,立即给五保户汤氏建个象样的灶。年轻干部也动了脑筋,在移民集中点,建一个既能方便集体又可照顾个人的移民灶。那是一个半圆形马蹄式的灶,用废砖砌就,抹上水泥。灶台上安十几个小锅,灶周围开十几个灶门,倒也美观实用。没多久,不办食堂了,各家又在屋墙角另起炉灶。
在灾荒的日子里
清理湖底的工人来了,推倒了田头寮
,砍倒了风水林,运走了旧木料。大坝合龙的时候,湖水席地而来,汹涌着象钱塘江潮水一样蔚为壮观,不时发出震耳的轰鸣声。从此,家乡的景观自是与前不同了。
天公不作美,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奇缺。在“瓜菜代”的日子里,湖水退在“三八二”线以下,饥饿的农民只好违背库区“自留地”戒律,在不显眼的边边角角播种蕃薯、南瓜、葫芦、扁豆和小麦,以济燃眉之急。那是1960年的夏天,父亲送来了三斤面粉、一包扁豆。我喜出望外,但又感到内疚,在搬迁的繁忙中,我帮助他什么呢?他那住在吉巷甲坡的二姆,因长期吃稀饭营养不良休克而去;住在大桥桃坪亭的细婶,困于贫病而离开了大家。
第二次移民
古田地处崇山峻岭之中,形成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河谷平原,是邑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水库淹没区又是全县最中心最大的平原,如城关、沂洋、平湖等平原。剩余的土地再容纳七千多户四万多人口,无疑是新的负担。
大旱逢甘霖,党和国家重新拨专款作为移民房屋补偿费,允许按人口定额重建新房。这是1962年、1965年间的事。移民的乡亲各凭自己的应得,或扩建、或重建、或独建、或合建新厝。
有的移民户因土地偏少,允许迁到外县。因此,在吉巷甲坡的两个堂弟又向建阳平沙迁移。在大桥宅里的八叔因缺乏劳力,改迁大桥镇旧街,后来又随女儿(国家干部)往将乐去了。迄今只剩下移民的第三代,也许他们不知道家乡移民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次移民,是由于县领导如实将移民艰难生活状况向上反映的结果。在那饥馑之年,敢于站在移民的立场上说话,的确是难得的。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却换来无情的批斗。因此,移民话题一度成为谈虎色变的“禁区”。
昙花开放的年头
1967年,正是湖水下落时间最长、库周露出土地面积最广之年。移民乡亲趁着公社、库区禁令松绑之机会,争占裸露的土地,私自垦殖。本村干部此时虽已被宣布靠边站,却依然勇敢地出面协调,采取湖水落一米平分一米、落两米平分两米的办法,众人皆大欢喜,减少和避免了因争地纠纷引起的斗殴事件发生。
那年8月,学校的红卫兵小将们也投入了武斗,对我们这些“黑帮”的监督也解除了。我趁此机会回沂洋,船到坂中搁浅了。下了船,沿福古公路旧路走着,顺便在路旁拔一棵花生,数一数上面挂着二十多颗花生。到了村口一望,连片的蕃薯藤随风荡漾着绿色的波澜。要是过去,谁舍得把“两收”、“三收”之地拿来种蕃薯呢?那年,新沙土上种的蕃薯喜获丰收,农民把它加工成蕃薯米,
供应附近各村及屏南边境的缺粮户。老父亲种的不多,加工后也卖了二十一元钱,好不欢喜。须知这是新湖蓄水十年来昙花开放的一年。因此,有人在议论着,如果当初把淹没线降低二三米,本村的土地就会保留着,在这等高线上大小乡村省去了迁移的麻烦。
向科学进军
沂洋移民后靠新村,后倚昆山之麓,前临翠屏湖之滨,呈现着新的自然景观,也面临着严峻的新的土地问题。早在公社化时期,农场要垦殖广堂殿蚕桑场而未成,欲经营枯水季节的库区,也不是理想的现实。留给保留户、后靠户的生产队的那几片薄田,秋收不多,冬藏不足,还要仰助于国家有限的回销粮。与我同年的堂叔,一年的工分顶不上半年的口粮。大家欲再兴家立业,各在悬念求索中。
在“向科学进军”、“发扬愚公精神”的口号声中,本大队苍岩村移民姚淑先毅然辞去了公社干部的职务,在广堂殿默默无闻地进行银耳人工瓶栽试验,不断取得可喜成果。随着农村体制的改革,大家又开始用新办法种果养鱼。散处在附近的宗亲也依样“种葫芦”,或栽菇、或种果而获益,先后摆脱了衣、食、住的困境。故以诗赞之:“开山种果行商始,植菌栽菇学技先。远近亲人逢庶境,欢呼改革艳阳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