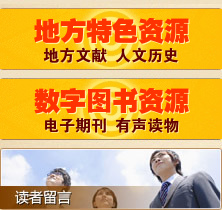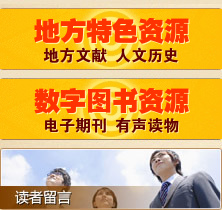江 山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孟之后最为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朱熹理学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想家、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之大,前推孔子,后为朱子。自汉以来,被封建王朝列入先儒先贤十哲者,唯独朱熹一人。因为朱熹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福建,其理学思想体系也主要形成于福建,所以他对福建文化教育影响最大。朱熹在古田培养了众多的理学门徒,为古田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以,也可以说朱熹对古田历史上的文化教育影响最大。

古田之所以成为紫阳过化之乡,第一个原因是朱熹曾来过古田讲学,促使古田教化弘开,人文蔚起。
古田与朱熹有缘,可追溯到朱熹的父辈。朱熹的父亲朱松,青年时曾经避地古田,与古田儒士林芸斋结为至交。有关这一史实,在《朱熹集》(《朱熹集》含续集、别集、遗集、外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中有一篇为林芸斋先生的遗文写的《跋》中说得很清楚。《跋》中写道:“先君子志尚高洁,不妄与人交。盖尝避地福之古田,得芸斋先生林公而与之游,爱其学识行谊有以过人,而惜其且将湮没于世。及仕于朝,为之延誉甚力,然竟不及试用,识者恨之。”(《朱熹别集卷七》)可见,朱松对这位古田朋友是很器重的,与之分别后还在朱熹面前经常提到他。因此,朱熹对这位从未谋面的林芸斋先生,自幼就有较深的印象。凑巧的是,林芸斋先生的儿子林师鲁,后来正好又成为朱熹的得意门人。朱熹后来在给林师鲁的信中提到:“某自幼年侍之先君子侧,则闻先芸斋公之名”。“虽先君子之挚友,如芸斋公者,亦无由一望其颜色而受教诲焉。孤陋块处,徒有向往之诚而无以自致也。”(《朱熹别集卷七》)然而朱熹并没有放弃来古田访问父挚的机会。能促成朱熹第一次造访古田者,恰恰又是一位古田的宿儒蒋康国。
蒋康国,字彦礼,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八闽通志·人物》载,“蒋康国尝从朱文公讲论文公《楚辞集解》,凡楚集皆质之康国,学者称鼎山先生。”
蒋康国与朱熹相识,原因是朱熹在尤溪县讲学时,蒋康国恰在尤溪任县尉,所以有缘经常在一起探讨《楚辞集解》中的疑难。蒋康国年龄与朱松相仿,所以朱熹尊称他为“蒋丈”。朱熹正是通过蒋康国了解到林芸斋先生情况的。朱熹说,“鼎山蒋丈来尉兹邑,因得从容请问,以访先君子之旧游,然后知芸斋公之没亦既久矣。”(《朱熹别集卷七》)遗憾的是,朱熹这次到古田“访先君子之旧游”,再也见不到这位林芸斋先生了。
从上述文字记载看,朱熹这次“访先君子之旧游”来古田,时间大约在乾道初年。但具体时间和到过什么地方都未见文字记载。这次朱熹来古田,主要是来了却一番心愿罢了。
朱熹第二次来古田,是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据古田杉洋《余氏总谱志》载:“子二度于尊师李讳侗祖籍地(注:据考证,李侗祖籍地在杉洋)游学讲论……”杉洋《李氏总谱》也记载:朱子“二至杉洋蓝田书院讲学……”是时,朱熹的高足林用中早已辞去尤溪“学政”一职,回古田办学。朱熹对林用中办学一事很高兴也很关心。朱熹曾在与择之书中说:“闻学中已成次第,甚善”;“闻县庠始教,闾里乡风之盛,足以为慰。”(《朱熹别集卷六》)这次,朱熹就是应林用中和余偶、余范等门人的邀请来古田的。其目的,一方面是来视察一下林用中和余偶、余范等人在古田的办学情况,一方面再来游览一下他的父亲曾经避地古田的山川秀色。朱熹在溪山书院呆了一段时间后,便在门人的陪同下,前往杉洋。古田杉洋在当时是人文发达经济繁荣的地方,那里有全省最早的书院之一蓝田书院。杉洋风景幽美。又是余偶、余范的家乡,也是他们的讲学之地,所以朱熹便应邀欣然前往。据说朱熹这次来杉洋,曾游览了杉洋的名胜“三井龙潭”,赞叹三井龙潭“胜似庐山瀑布”。宋人余宋兴于淳熙十一年所撰的《龙井记》提到:“平沙林择之来视,矍然曰:‘庐山之卧龙、西涧、谷帘、漱玉,无如是也。’”据说朱熹还到离杉洋数十里开外的廖厝原始森林留连,并在石壁上题诗而返。此后该处便被名曰“题诗林”。
朱熹这次来古田,游览了许多地方,使古田又一次濡沐圣贤之文光。对朱熹而言,似乎也为他后来在庆元党禁时,决意来古田避难预埋了心理准备。
朱熹最后一次来古田,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寓贤》已有明确的记述:“宋朱熹,字仲晦,新安人。庆元间韩侂胄禁伪学游寓古田,宗室诸进士与其门人构书院延而讲学。所寄寓处附县治者,匾其亭曰‘溪山第一’。往来于三十九都徐廖二大姓。尝书‘大学户庭,中庸阃奥,文章华国,诗礼传家’。螺峰、浣溪、杉洋诸所皆其游息而训诲也。文公尝曰:‘东有余李,西有王魏。’盖自纪其众乐云。”
促成朱熹这次来古田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庆元党禁。庆元初,南宋朝廷内部党同伐异的斗争呈白热化。朱熹好友赵汝愚被罢相,大权悉归韩侂胄,一场内部斗争,严酷至极。据《宋史·列传·道学》记载,庆元元年(1195年), 朱熹得罪韩侂胄,遭落职罢祠。其时即谣诼四起,有欲问斩朱熹之说。朱熹被夺职后,回到武夷冲佑观避祸。庆元二年二月后,朝延攻“伪”不断升级,先是斥朱熹等人为伪党,继而说是逆党,后则定为死党。列党禁的人物达59人,朱熹名列第五。明·李贽《藏书·儒臣传》还载,当时对全国的官员、科举考生都要进行全面的政审,凡与“伪学”有牵连者,考生不准参加乡、会试,官员则或罢或贬。大批儒家经典著作都要除毁,大有秦时焚书坑儒重演之势。处于这种险境,朱熹曾自号“遁翁”。在上述这么严峻危险的形势下,朱熹的唯一选择就是要遁避了。
朱熹之所以会遁避到古田来,其根本原因则缘于古田有一批忠于他的门人。《宋史·列传·道学》载得很清楚,“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自别其非党。”原来与朱熹交游的朋友和跟随朱熹的门人,贬的贬,匿的匿,逃的逃,叛的叛,这种风云骤变、世态炎凉的逆境,又给朱熹带来沉重的打击。更有甚者,党禁时,朱熹最得意的门人蔡元定遭遣送管制,已客死途中;女婿黄干自然也要被株连,流寓古田。建阳是朱熹长期讲学受徒的理学基地,因此,当时的建安县令也受牵连而被降级,还规定他永世不得再做地方长官。此时,贫病交加、仇怨相攻的朱熹更显得孤悽无助,大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而这时,朱熹在古田的门人,却都表现了他们对理学的坚定信念和对朱熹的一片忠心,能和朱熹患难与共,险夷不变其节。林用中“从文公游最久”。党禁时,他们师生互相慰藉。朱熹在危难中很思念他,写信给他说:“秋冬间能同扩之一来慰此哀苦否?”同时,也十分关心林用中兄弟的安危,曾写信告诫林用中兄弟:“切不可与人往来。至如时官及其子弟宾客之属,尤当远避,勿与交涉,乃可自安。”(《朱熹别集卷六》)古田门人林夔孙更是坚定紧跟朱熹直至朱熹逝世。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党禁起,学者更事他师,惟夔孙从文公讲论不辍,文公易箦之日曰:‘道理只是如此,但须做坚苦工夫。’”朱熹在给其女婿黄干的一封信中也说到,在“亲旧皆劝谢绝宾客、散遣学徒”时,“书院中只有古田林子武(夔孙的字)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读书颇有绪。”(《朱熹续集卷一》)在“朋从零落,道学寡助”之时,又有古田的林大春去看望和安慰朱熹。朱熹后来在给林大春的信中说:“去冬枉顾,幸得数日款奉名理,感慰至深。”(《朱熹别集卷五》)朱熹在“疾病益侵,仇怨交攻……今年绝无朋友相过”时,却想起了古田的余偶,写信要他“冬间能枉路一顾”(《朱熹集卷五十》)……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古田籍朱熹门人给朱熹带来最大慰籍,他们为了老师的安全,把朱熹请到古田来避难。
考虑到当时的险恶处境,考虑到古田门人给他的慰藉,且古田是他曾经游历过的地方,庆元三年初,朱熹就在林用中、余偶等门人侍陪下,从建阳来到古田。
朱熹这一次入古路线,应该是从闽北沿水路到古田水口,而后再由陆路到古田县城。
水口是闽江中游要镇,是闽北到省城的水路要口。宋太平兴国时曾设县治,后改设巡检司,并设有驿站。朱熹一行夜泊水口,触景生情,融情感与哲理于眼前景物之中,写下了历来脍炙人口的《水口行舟》两首诗。其一:“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其二:“郁郁层峦夹岸青,青山绿水去无声。烟波一棹知何许,鶗鴂两山相对鸣。”朱熹在这两首诗中,借自然景象,表达了他在罹学禁之祸时的一番心态。他相信,庆元党禁的“夜雨”和“风浪”都将会消失,他憧憬着他的理学前景如青山绿树,依然美好。当然,眼下的形势毕竟十分险恶,此时身如烟波一棹,悄然漂去,难免也产生一番惆怅和无奈之情。
水口驿站到古田县城,交通方便,有舆马通行,不足一日之程便到古田县治所在。古田溪山书院就在城东北。离这不远就是林用中兄弟的家乡西山村。明邑名士周于仁《溪山书院记》云:“县治东北去雉堞外不数武,平地突起冈阜,山势奇郁,下环双溪,四周萦注。”这里原有一亭,叫做双溪亭,后林用中等人把它扩建成书院,现在便成了朱熹避难的第一个立足点,在此设帐讲学。党禁方严,朱熹在建阳毕竟是过着孤独无助、“朋从零落”、“仇怨交攻”的哀苦日子。一到古田,远离其时闽北的是非之地,心情自然一下子好了起来。朱熹看到这书院所在地山奇水秀,便挥毫题下“溪山第一”四个大字。可惜“溪山第一”四字石刻于1958年古田建水库时没入湖底。在溪山书院前面,林用中另建一亭曰“欣木亭”。朱熹登览欣木亭,欣赏美景,想到又有林择之等忠心耿耿的门人相陪不免心情舒畅,即兴写下《题林择之欣木亭》这首诗:“危亭俯清川,登览自晨暮。佳哉阳春节,看此隔溪树。连林争秀发,生意各呈露。大化本无言,此心谁与晤。真欢菽水外,一笑和乐孺。聊复共徜徉,殊形乃同趣。”
朱熹除了在溪山书院讲学外,还到过附近的几个书院讲学。其一,浣溪书院,在八都,离溪山书院十余里,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朱熹曾为之题匾。其二,螺峰书院,在九都螺坑,离溪山书院二十余里,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朱熹的女婿黄干讲学于此,朱熹曾题有“文昌阁”三字。相传朱熹的女婿在螺峰书院讲学时,有一次朱熹去看望他。因家境贫穷,女儿只能以麦饭葱汤招待。朱熹观察到女儿面带愧色,便即席吟诗一首安慰她。这便是有名的《慰女儿贫诗》,诗曰:“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其三,魁龙书院,在林用中家乡西山村,离溪山书院十里许,此书院至今尚保存完好。
朱熹在溪山书院讲学的同时,传说还为林用中的家乡造风水,设计了两口井和一条玄字形的道路。同时,还到过离城不远处的平湖富达村的“蓝洞”游览。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有一篇朱熹写的《蓝洞记》,便是他游览后写成的。
有关蓝洞的传说是这样的:古田县平湖富达村始祖蓝文卿原居闽侯雪峰,因捐田资建寺有功德,唐禧宗封檀樾(施主)蓝文卿为威武军节度使。后来蓝文卿再施田庄,以至资产已尽。雪峰寺真觉大师指一牛嘱乘前行,至富达蓝洞,牛化为石。蓝文卿即以此处为兴基之所。后子孙繁衍,形成村落,即富达村。蓝文卿捐资建寺确有其事,但牛化为石等当然是神化的传说。据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卷二·山川》记载,蓝洞又名白鹿洞,在富达村。唐蓝文卿隐处。朱文公撰有《蓝洞记》一文,对蓝洞及其四周景物描写得十分形象具体。可惜此文没有落款和撰写的时间,在朱熹文集中被编入《朱熹外集卷二》中。(全文见文摘篇《蓝洞记》)
朱熹在溪山书院呆了一小段时间后,考虑到古田县城毕竟离闽北较近,又是县治所在,目标太大,便应门人余偶、余范的邀请,转移到杉洋蓝田书院。杉洋离古田县治有一百六十多里,地处宁德、罗源、屏南、闽侯几县交界处,远离闽北。但此地又是当时较发达的山乡,人口万余,余、李两大望族螽族于斯,又是李侗的祖籍地,而且朱熹十几年前曾造访过,无疑是朱熹喜欢前往避难的安全之所。在这里,完成了他教学生涯最后阶段。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机构。宋时盛行讲会制度,名师大儒,可以在几个书院轮流讲学,听者也不限地区和本院生徒。学生远道慕名而来求学是常有的事。”(《中国书院史》)杉洋人崇文重教,地邻五县,因此,慕名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新旧生徒咸集,书院盛况空前。据《古田县志》和余、李两氏宗谱记载,听讲最多时近千人。许多朱熹原先的门人也聚集到朱熹身边。蓝田书院内曾设有一“公座”,“公座”的木牌上刻有“十八门人录”。这十八门人都是当年知名的高足,在《八闽通志·人物》中都有记载。其中,宁德籍的有三人:“陈骏,字敏仲,举进士,登朱文公门”;“龚郯,字昙伯,早从朱文公学,与福安杨复同门友”;“郑师孟,字齐卿,受业于朱文公门,勉斋女婿”。长溪籍的有两位:“杨楫,字通老,与杨方、杨简俱师事朱文公,为高弟,人称三杨”;“黄干,字尚质,师事朱文公”。福安籍一人:“杨复,受业朱文公之门,与黄干(勉斋)相友善,学者称信斋先生”。其中还有朱熹女婿黄干(勉斋),高足廖德明。据称廖德明祖籍在古田杉洋东溪村,后迁顺昌。《八闽通志》称:“学禁方严,德明确守师说,不为时论所变”。还有一位浙江永嘉人周端朝。以上均为外籍门人。其余9人,有林用中等,都是古田籍门人,其中杉洋本村的有余偶、余范等人。
朱熹在蓝田书院讲学期间,李昂为堂长(即院主),直学李元鼎、李言可为书院执权,制定条规(见《李氏宗谱》)。蓝田书院邻近还有几个书院。有朱熹门人余偶、余范读书过的擢秀斋,有余范曾执教过的兴贤斋,还有谈书书院。朱熹在杉洋时,也经常到这几个书院去讲学。因此,历代民间便有朱子一日教九斋的神化传说。朱熹在杉洋讲学的日子,无疑是很安心很充实的。他为杉洋留下了许多墨迹。他为蓝田书院题写了院名。该院名石刻至今保存完好,边款刻有“堂长李昂直学李元鼎立石”及“宋丁未春三月”字样。有关“蓝田书院”题匾,杉洋《余氏族谱》中载有余偶《蓝田书院鳌鱼吐水水墨集》一文,文中说:“朱文公庆元三年遭害避居乡间,集门人于蓝田……挥如椽之笔,以鳌鱼所吐之水磨墨,题‘蓝田书院’匾额。”所谓鳌鱼者,系书院内有一巨石形如鳌鱼,且有泉水涌出,故云。
蓝田书院内有朱熹书写的对联两副。前厅左壁一副为“春报南桥川叠翠,香飞翰苑野图新”;右壁一副为“雪堂养浩凝清气,月窟观空静我神”。后来有人把它摹到杉洋凤林祠后厅左右壁上,朱熹笔迹幸得保存。
蓝田书院不远处有一泉水池,池边石壁上有朱熹所题的“引月”二字,署号茶仙。据说朱熹嗜茶,以茶仙自号。此石刻仍保存完好。此处系蓝田八景之一,称为“天池引月”。朱熹还为擢秀斋题写一副楹联:“碧海开龙藏,青云起雁堂。”此幅楹联木刻历代以来一直珍藏在一余氏族人家。此联书法笔飞墨舞,流畅一气,其字体曾经省博物馆等单位专家认定,实属朱熹笔迹无疑。
据《书史会要》一书载,“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另据朱熹的“议书”所称,他学书少时喜学曹孟德书,后来改法于颜。朱熹在杉洋留下的几处现存完好的笔迹,可谓诸体皆备,丰富之至,殊为珍贵,非他处所能比。现已成为古田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庆元三年,朱熹在古田讲学大约半年时间,之后便在宁德、长溪的几位门人邀请下到宁德、长溪,随后取道浙江,又回到闽北。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逝于建阳。
朱熹三次到古田,前两次仅仅是有“向往之诚”,来古田做短暂逗留而已,未必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三次来古田,是朱熹理学炉火纯青之时。朱熹以蓝田书院和溪山书院为一东一西两个中心点,在各个书院讲学授徒传播理学,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生徒众,声名远播,留下的诗文墨迹多,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从而使古田成为紫阳过化之乡。
古田之所以成为紫阳过化之乡,另一个原因是,朱熹为古田培养的一大批得意门人,成为朱子理学在古田的忠实传人。
朱熹的古田籍门人有史可查的约有二十人。这些门人都是古田儒林学子中的佼佼者,不少人都有功名和成就。他们师从朱熹之后,在继承和弘扬朱熹理学方面更是各有建树。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对朱熹毕志相从,对朱熹理学坚心不喻,师生关系十分密切。是他们对这位圣贤的崇拜和忠诚,使古田有缘接纳圣贤履迹;是他们对理学的师承和薪传,促进了古田文化教育的繁荣兴盛。
林用中是朱熹最得意的门人,《八闽通志·人物》载:“林用中,字择之,始从林光朝学,后闻朱文公授徒建安,遂弃举业往从焉。”林用中初拜朱熹为师,凭他的悟性与学识,即得到朱熹的赏识。朱熹在给林师鲁的信中说:“去年林择之不鄙过门,以讲学为事,怪其温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老于学者。”(《朱熹别集卷五》)朱熹特为林用中改字曰“择之”,并为之写序。朱熹在《林用中字序》中赞扬他“志之高,力之久,所闻之深而所至之不可量也。”(《朱熹集卷七十五》)《八闽通志·人物》和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文公尝称其通悟修谨,嗜学不倦,谓为畏友。”林用中与建州蔡元定、范念德及闽县黄干(勉斋)一样,成为朱熹身边最得意的四大门人。他深得理学之精髓,其学识与被喻为闽学干城的蔡元定齐名。朱熹给林用中书中所说:“择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闻益论尘土满襟耳。”(《朱熹别集卷六》)
林用中从他师事朱熹起,直到庆元党禁,长期紧跟,如《白鹿洞志》所言,“林择之从文公游最久”。朱熹每有外事活动,如到长沙“岳鹿会友”,到江西“鹅湖论辩”,到庐山“鹿洞讲学”等等,必偕林用中作伴同行。
朱熹对林用中的赞赏,屡屡溢于言表。朱熹给他人的书信和文稿中,有五十余篇都提到并赞扬他。如,朱熹答许顺之书中说:“择之所见日精,工夫日密,甚觉可畏。”(《朱熹集卷三十九》)在答何叔京信中说:“古田林君择之者在此,相与讲论,其人操履甚谨,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胜己而已。”(《朱熹集卷四十》)在答石子重信中说:“伯崇(即范念德,朱熹四大门人之一)精进之意反不逮前,择之见趣操持愈见精密。”(《朱熹集卷四十二》)在答李深卿书中说:“择之讲论精密,务求至当,似未为过。”(《朱熹集卷四十五》)……诸如此类赞语,不一而举。朱熹在给他人的信中,还特别体现了他们二人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朱熹在给其挚友吕祖谦的信中说:“择之来此相聚甚乐。”在给张敬夫(张栻)的信中说:“择之久不相见,觉得病痛日深。”(《朱熹集卷三十一》)在给许顺之的信中说:“今岁却得择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后多是悠悠度日,自兹策励,不敢不虔。”(《朱熹集卷三十九》)朱熹在给何叔京的信中说,他在学术探讨中自觉得“无进步处”,“心志亦不复强”,希望得到他人相助时,得林用中“此公之力为多也”(《朱熹集卷四十》)。朱熹与林用中书信往来十分频繁,多达五十余件。信中所述内容广泛,除了大量篇幅在探讨学术之外,其他如时政、艺术、家事、友情,无所不及。信中还特别体现了朱熹对这位学生的器重和深情。朱熹在给林择之的一封信中说:“思与吾择之相聚,观感警益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虚言也。”(《朱熹集卷四十三》)“某近觉向来乖缪处不可缕缕……朝夕惴惧,不知所以为计。若择之能一来,辅此不逮,幸甚。”
朱熹和林用中的唱酬诗特多。乾道丁亥秋,师生同往长沙岳麓会友,朱熹、张栻、林用中三人登南岳互相唱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首,编成《南岳唱酬集》。岳麓会友后东归,“缭绕数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师生二人一路唱和,“掇拾乱稿,才得二百余篇”,编成《东归乱稿集》。
综观朱熹文集,不难看出,朱熹与林用中的师生关系,早已升格为亲密的师友关系。朱熹在与他人的诗文往来中,总是称择之为“畏友”、“仁友”、“友人”。虽是自谦之称,但事实也应如是。
朱熹与林用中的亲密关系,还可以从其他一些事例中见之一斑。朱熹在给祝直清书中说:“恨此中前辈寥寥,幸得古田林择之邀至家馆,教塾、 二人,其见明切。”(朱熹遗集卷一)可见林择之还当了朱熹两个儿子的私塾老师。又如,朱熹自乾道九年始,“为贫谋食”,在南宋时被誉为“图书之府”的建阳崇化书市建立同文书院,撰著编印书籍出售,其经费往来,常交林用中管理。朱熹在古田的礼尚往来,如祭奠友生之类,也多叫林用中代行师职。
朱熹在古田的门人中,与林用中有直接关系的还有几个人,其一就是他的胞弟林允中。林用中师从朱熹后的第二年,也把他的弟弟带来拜在朱熹门下。朱熹也为林允中改字曰“扩之”,也为之写了序。朱熹在《林允中字序》中说:“明年,扩之亦来,视其志与其才,信乎其如择之言也。”“允中从予游,今四五年矣。深察之,则其为人盖晦于外而明于内,朴于外而敏于中者也,是以予有取焉”。(《朱熹集卷七十五》)朱熹与林允中时有书信往来和诗词唱酬。朱熹在与他人的书信中也多次赞扬他。在给林择之信中说:“得扩之朝夕议论,相助为多。幸甚!”(《朱熹集卷四十三》)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扩之来此相取,极有益。其专志苦学,非流辈所及。”(《朱熹别集卷六》)
林用中和林允中兄弟在弘扬理学方面对后世影响颇大,世称他们为“二林”。林氏后人历代以来在大门边都有这样一幅对联:“十德衣冠裔,二林理学家。”
朱熹的古田门人中,被林用中一同邀至朱熹门下的还有三人,他们是林师鲁、林大春和程深父。朱熹在与林师鲁书中说:“去年择之不鄙过门,……因扣其师友渊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则向所闻吾芸斋公之子也。”(《朱熹别集卷六》)
林师鲁系朱熹父亲朱松的挚友林芸斋先生之子,林用中曾从学于他,可见林师鲁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师鲁投入师门,自然得到朱熹的赏识。朱熹称赞他“美才高志”。朱熹在答林用中的信中称赞“师鲁论解极佳”。因为朱熹与林师鲁多了一层父辈友好的关系,朱熹与师鲁的感情也特别深。朱熹曾应林师鲁之请,为其先父林芸斋先生的遗文写了跋。林师鲁志长命短,他病重之时,朱熹“闻师鲁遽不起疾,深为悲惋”。听到师鲁去世的消息,朱熹还为他写了一篇言辞十分深切的祭文,专托林用中代为祭奠。朱熹在祭文中称,“如师鲁之才之敏,乃不克究其业而止于斯,吾徒二三子失良友之助,徒不陨涕相吊?”(《朱熹别集卷七》)
林大春,字熙之,号造斋。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林大春,朱文公门人也。尝题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敢不修整。”从朱熹与林大春长期书信和诗文往来中,可以看出他们深厚的师生情谊。朱熹文集中收有送林熙之诗五首。诗中论交论道,感情至深。如第一首:“君行往返一千里,过我屏山山下村。浊酒寒灯静相对,论心直欲到忘言。”第四首:“十年灯火与君同,谁道年来西复东。不学世情云雨手,从教人事马牛风。”
程深父,与朱熹的关系也是十分亲密的。师生之间都有书信往来。可惜程深父太早去世。深父病逝之时,朱熹“深为悲叹”,还备有状及香茶,并要林择之兑钱一千贯“致此微意”。(《朱熹别集卷六》)
在朱熹的门人中,林夔孙是跟随朱熹最坚定者之一。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林夔孙,字子武,号蒙谷。朱文公门人也。文公尝口授讲议,俾讲于白鹿洞。”林夔孙既是朱熹门人,又是朱熹得力助手。党禁时,林夔孙跟从朱熹更紧。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党禁起,学者更事他师,惟夔孙从文公讲论不辍。文公易箦之日曰:‘道理是如此,但须做坚苦工夫。’”朱熹在给其婿黄干的信中也提到,党禁之时,“亲旧皆劝谢绝宾客,散遣学徒”,这时,“书院中只有古田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读书颇有绪。”(《朱熹续集卷一》)
古田西山村有“二林”,而在古田杉洋则有“二余”,即余偶和余范,同是朱熹的高足。
余偶,字占之,号克斋。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说他是“朱文公高弟也,与林用中齐名。尝与吕祖谦、黄干(勉斋)书问往来,讲明义理。”有《克斋集》行世。余范,字彝孙,与余偶同乡、同窗,同时为朱熹门人。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和清·乾隆版《古田县志》也均有记载。从朱熹文集中可以看出朱熹与余偶、余范多有书信往来,而且朱熹与“二余”师生关系十分密切。如朱熹在给林用中的一封信中说:“二余在此日久,占之警敏,彝孙淳静,皆可喜。”(《朱熹别集卷六》)朱熹一些外出游览,如朱熹罢郡后游览庐山,游周敦颐的亭、院等,都有余偶陪同。朱熹文集中有一封给余范的长信,信中探讨了许多问题,字里行间可看出朱熹对余范的谆谆教诲。朱熹在党禁后的苦况中,对“二余”特别思念。在给余偶的信中说:“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仇怨交攻,盖未知所税驾也。今年绝无朋友相过,近日方有至者,只一、二辈,犹未有害,若多,则恐生事矣。无由会面,远书不能尽怀,不知冬间能枉路一顾否。”(《朱熹集卷五十》)在友生零落,且恐生事,不想有多人相过的情况下,却想着余偶来顾,可见朱熹与余偶关系之亲密。
从明·万历版《古田县志》和朱熹文集中还可看到,傅子渊也是朱熹的得意门人。傅子渊,字梦泉,约于淳熙十二年入师门。朱熹很看重他,在给陆子静的信中称:“子渊去冬相见,气质刚毅,极不易得。”朱熹与傅子渊常有书信往来。《朱熹集卷五十四》中就收有《答傅子渊书》四件。朱熹对傅子渊的学习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信中称赞“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复愚昧所能窥测。”(《朱熹集卷五十四》)
明·万历版《古田县志》载,“程若中,字宝石,尝从文公学。嘉定中特奏名,躬行无伪,终身不违于礼。有《槃涧集》行世。”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张棫,字先之。绍定二年进士(特奏名),游朱子之门。”明·万历版和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还载有程伯荣、林好谷、林充之、苏龟龄、黄有开等人“皆游朱子之门”。据古田杉洋《余氏族谱》和《李氏族谱》载,还有余亮、余畟、李言可、李昂等人,也都是朱熹的门人。
朱熹在古田的这么多门人,他们在学术上多有建树,不少人还取得功名,且多有著述行世,有一部分则成为古田各个书院的掌门人。他们在古田各地弘扬朱熹理学,代代相传,使古田成为理学之乡。紫阳过化,与这一大批门人是密切相关的。
这里,还有几个人物与朱熹有密切关系,在古田弘扬朱熹理学方面有过贡献和影响的,也值得一提。
黄干,字直卿,闽县人。系朱熹的女婿,朱熹理学的得力继承人。如真德秀所云:“惟公之在考亭,犹颜曾之在洙泗。”(真德秀《勉斋先生祝文》)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寓贤》载,庆元党禁时,“亦以伪学之禁,寓九都族人家。与朱晦翁讲道论德,悠然也。”朱文公避难来古田溪山书院时,黄干在螺峰书院讲学。后来又陪同朱熹到杉洋蓝田书院,协助朱熹讲学论道。同时,黄干与林用中是朱熹四大门人之一,与余偶、余范交往颇深,在为古田弘扬理学方面,黄干也融入了古田籍门人的队伍中去。
李侗、李友直父子。李侗是朱熹的老师,对朱熹影响很深。据考证,李侗祖籍在杉洋,李侗二十四岁后才迁居延平。“李侗子友直,绍兴丁丑科进士,授铅山令,与朱晦庵先生为友。时禁伪学,迁寓一都谷口小鲎,子孙随家焉。”(见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寓贤》)可见李氏父子在古田弘扬理学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杨易。杨易是“浙江山阴人,官拜兵部侍郎,与晦庵朱文公同为理学。因谏韩侂胄丞相,贬为杉关(即杉洋)巡检。”(见《余氏总谱志》)杉洋人因尊崇他,在他死后将其奉为通乡拓主,在杉洋建有槐庙、东山庙奉祀他。群众尊敬和宣传杨易,实际上就是在崇拜和宣扬朱熹。
赵汝腾。赵汝腾系宋太宗七世孙,居古田。宋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曾拜端明学士兼翰林学士,知泉州。素与朱子相友善。其题朱子像云:‘理精义著,德盛仁熟,折衷群方,如射中鹄,绝学梯航,斯文菽粟。在庆元初,中行独复。’朱子诸赞,此为第一。”(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赵汝腾靠着他的特殊地位,宣传朱熹,宣传理学,无疑地对理学在古田的传播产生一定的效应。
康太保。清代杉洋名士余廷章《蓝田·左边城外志》中载“……晦庵朱文公理学宋时真儒,时衰不知其学。敕命太保赐姓惟康欲剿文公。其辈亦为理学,自废而亡,不欲真儒为伪学者殃。因镇杉关新修庙宇,永荐馨香于重阳日吉云。”太保庙除了杉洋外,古田县内还有多处。乾隆版《古田县志》记载:“朱子避地玉田,时韩侂胄遣人迹其后,将甘心焉。是人宁自刎死,不肯杀道学以媚权奸。邑人义之,祀于溪山书院对面,即今之太保庙也。”古田还有一个传说,庆元三年江西参将周江胡、罗协奉旨到古田追捕朱熹,也是在两难之中周、罗选择自杀。后被西山村人奉为拓主,立庙奉祀周、罗二将,庙曰虎马将军殿,在魁龙书院对面,至今尚存。
从以上这几个人的事例说明,古田与朱熹、古田与朱子理学之间,冥冥之中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渊源关系,为古田成为紫阳过化之乡,也增添了几笔浓墨重彩。
由于先贤过化,朱熹与朱子理学对古田社会文明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是理学薪传,人才辈出。
朱熹在来古田讲学之前,已经有了一大批古田的得意门人;来古田讲学之后,又涌现出一批新的门人。加上朱熹的友人、亲眷,在古田汇成一个庞大的师承队伍,成为弘扬理学的骨干。这些人又培养出再传弟子,如此代代薪传,绵延不断。特别是朱子理学在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中确立了统治地位,成为精神支柱之后,朱熹的《四书集注》及朱子学的经学注释成为历代教科书和科举考试依据之时,古田学子靠着代代正宗师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单南宋庆元至元初,古田就出了90名进士。古田宋代有经史子集著作者9人,计11种,而朱熹门人占5人7种。清代福州知府余景熹序《古田县志》云:古邑“长材秀民,通经求能文章者,宋元为最盛。”从元、明至清,又出现了张以宁、余正健、甘国宝、曾光斗等一大批杰出人物。
二是亲临讲学,教化宏开。
朱熹来古田讲学,以溪山书院与蓝田书院为中心点,足迹遍及古田各个书院。朱熹一生办教育,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对古田教育产生巨大影响。朱熹办学的教育宗旨、办学规程、教育阶段、教学原则、形式、方法等,都会渗透到各个书院中去,健全了古田书院的建设。为继承朱熹遗志,二林、二余等众门人主持古田各处书院讲学论道,使古田书院教育的面貌焕然一新,教育层次也更上新台阶,教育理念也发生变化。从此,古田办学之风盛行,人才荟萃,如清·乾隆版《古田县志》所说:自朱熹来古讲学后,“自是名贤继起……教泽之渐渍玉田者渥矣!”古田历代以来,文化教育事业一直跻身八闽前列。历代古田民众尊师爱教,培养人才之风浓厚。古田大东地区崇文重教之风尤为突出,一直延续至今。这一良好风气与朱熹曾在蓝田书院讲学是密切相关的。如清代福建学政翰林侍讲学士朱珪所撰《蓝田书院碑文》所言:“……育养人才,涵濡沐浴多士,得幸古田之蓝田书院。”
三是名人效应,开创文明。
庆元党禁解除后,朱熹被谥为“文公”,声名与代俱显。朱子理学被推崇到儒学正宗的地位。古田人历代以接纳朱熹来古田避难讲学为荣,朱熹被尊为圣人偶像加以崇拜,崇尚朱熹道德伦理哲学之风日盛。朱熹涉足的许多地方都建有朱子祠,祭祀活动历代不衰。南宋以来,古田凡有学堂,必祀朱子;普通人家,厅堂上都挂有朱熹书体的“行仁义事,存忠孝心”、“忠孝持家远,诗书处世长”等楹联。朱熹作为圣贤的形象和他的理学历代深入人心,形成“人文崇孝悌”、“家贫亦业儒”的风尚,因而必然给古田带来了封建社会的文明景象。清·乾隆版《古田县志》载:古田人宋以前受教育程度差,信巫好斗尚鬼,不开化,欠文明。《福建通志》称,自古古田邑民“往往逋赋,好斗喜讼,颇易动难安”。而“至朱晦翁避地至此,羲文周孔之道,洋溢溪山,理学文章甲于他邑;而忠孝义烈之风至明季而大畅。”(清·乾隆版《古田县志》古田知县辛竞可序)“自宋至今,士君子敦本务实,小人食勤啬用,守朱紫阳遗训,冠婚丧祭,犹醇朴之风。”“古田古属峒氓椎髻跣足固无文可言,自宋紫阳朱子过化后户诵家弦之风为之一振,庶几称海滨邹鲁。”(民国版《古田县志·艺文》)就较边远的杉洋来说,自朱熹讲学之后,文明景象历代相延。清代古田县令万友正在《重修蓝田书院序》中称:“至其地,其秀者敦诗书而尚礼义,朴者安谨愿而守耕凿,休休乎太古之风,窃心异者久之,询知为紫阳过化之乡。”
四是增强素质,社会进步。
古田因分得朱熹一脉真传,其理学渊源向古田文化多元化渗透,对古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朱子理学的广泛传播,使古田文化教育基础雄厚,人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提高。人文发达,社会必定走向繁荣。古田自南宋以来属望县,元代时属上县,至明、清两代古田人文经济在福州路(府)十数县中名列三、四。正如元代吴海《送郑训导》所言,“古田在昔,提封之广,居民之众,邑里之华,文物之盛,盖彬彬焉”。清·乾隆版《古田县志》称:“自宋迄今,诗书弦诵,俊采翩翩,邃谷深山,人烟霭霭;而居民辐辏,城市喧填,几几乎与通都大邑并繁庶矣。”
感谢朱熹,感谢朱熹的众多门人,为古田八百年文化教育和封建文明史写下光辉的历史篇章。